
韶华何日返当年 逝矣去悠然
一
童年对我来说好像并非只在嬉戏中度过,稚幼的我并不喜欢唱歌跳舞。记得所读的幼儿园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操场角落长满了狗尾草、蒲公英、豆腐草……那时常常一个人走进草丛,手上把玩几茎小草就可以独坐老半天。
头脑里满是古怪的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有什么东西?”“那地下呢?”“我死了再到哪里去?”……尽管大人们明白地回答说,我是从河里捡来的,但我知道他们在骗我。家里手电筒的电池,常常因我用来照射天上到底有什么而将电用光。
那时常常离开同龄的玩伴,坐在小河边,思绪于是随流水漂走,仿佛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梦想着有另一片天。
看越剧《红楼梦》虽不懂剧中情节,却也哭成了泪人,别的没学会,却偏要像黛玉葬花一样去捡园中落英,并也悲悲戚戚,仿佛自己也正生死飘零。
从大人那里听了很多童话、寓言、神话故事,在没人的时候便扮演故事中的人物,于是家里的毛巾、床单,父母的围巾、帽子都会成为道具。镜子前的我就可以自编自导自演地玩上一整天,常常在听到开门声时,惊惶地收捡所有,手忙脚乱地一股脑儿塞进柜子。
父母是很开明的,他们偶尔也会坐在床前,满怀兴致地看我和哥哥演戏。于是大床成了戏台,哥哥常常扮演坏蛋,而我自然就是正人君子,有时演着演着还会入戏掉泪呢。
作中学校长的父亲在家里为我设置了一块做练习的黑板,黑板前的我便会一本正经地去教授、训斥坐在小凳上,哪怕比我还大的小孩。
暑假,父母会让我到乡下亲戚家去住一段日子,我喜欢乡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在那里可以不顾母亲训教的淑女规矩,遍田野跑,放声高歌。
我喜欢乡下人的朴实与坦诚,喜欢他们咧嘴大笑和大声吆喝,喜欢他们拍拍双手就可以顺手拿东西吃的麻利、歪身一倒就可鼾声如雷的随便。在晒场头大人的腿上我听过很多村野怪事,也跟随大孩子学会了不少农家活计。回家时,衣兜里总少不了为父母带回些野果,手里拿着沿途采摘的野花,甚至还有绑在线上的蜻蜓,因为我一直惦记着父母蚊帐里有赶不走的蚊子。
[NextPage]
二
稍大一点,按母亲的话来说是人小心大,那时我常感人事的不如意,世人为什么那么尔虞我诈?为一点小事亲人可以反目成仇?出了事的家一墙之隔的邻居可以安之若素……为了维持一种理想的生活我便开始幻想,并拒绝成为现实的主人,也因为这种拒绝,我变得沉默、孤独、多愁、善感,常常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身边与我同处在花季年龄的少男少女们崇尚时髦、追赶明星、陷入早恋。
在我的世界中,不喜欢城市的忙碌与慌乱,而向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喜欢“目断吾庐小翠微,斜阳外,百鸟傍山飞”的情趣,喜欢“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超然。
我喜欢独自去看天上千变万化的游云,去观水面转瞬即逝的浮沤,去听风中万物冲击的撕扯……让内心的不平在大自然中得到认同和化解。即便是“缥缈孤鸿影”,却也不愿同流于无谓的嬉戏。
将自已关闭于个人空间,在那里进行自我对白和自我安抚,以保有自己独特的古朴和忧郁。在别人眼里我是傲不可近、深不可测,甚至父母也常因我的多变而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虽然因为“鹤立鸡群”而常常成为众矢之的,但我也不愿“委曲”自己与众同流,也因为这种敏感和多愁,我有了比同龄人更丰富和更深刻的内心世界。
那时,我常怀疑人们终生忙碌追求的生活是否真实?用金钱换来的一点快乐是否有意义?信誓旦旦的爱情是否永恒?是的,一方面我怀疑,另一方面我又渴望——渴望有另一种答案和另一种追求。
那时的我,敏感、脆弱、多情而又寂寞。我一面保留自己的个性,一面又一次次否定它,别人看来我是倔犟的、任性的、情绪难定的。
早早的,我就预感自己会热闹而又孤独地走向死亡,带着一颗伤感而失落的心远去,去寻找所谓的真实,而掬捧起的双手里却只盛满着我的泪与愁。虽不谙世事,内心却有久经沧桑的悲凉,形单影只的我常常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
[NextPage]
三
那时最留得住我的是家里的玫瑰园。由于爷爷的富有,在我的童年,家里还有很多住房,一片竹林和一个花园。竹林在住房对面,花园就在房子后面,种有一架月季和一架葡萄,架下有一石圆桌,那是父亲对弈、母亲做针线、我夏天做作业和家人乘凉的地方。打开花园后门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和几排护堤的竹子。把它称作“玫瑰园”是因为它带给人一种温馨。春天架上满是盛开的粉红色月季,花形硕大,娇艳欲滴。夏天那满架青翠透明的马奶葡萄,像悬挂的一串串翡翠。知足的母亲便会一边吃葡萄一边对看书的我说:“这就是神仙的生活吧。”秋天园里的菊花又常常使人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散淡与适意。冬天的阳光从架上投射下来,搬张藤椅就可以蜷缩在里面,把自己送到爪哇国去。
常常是抱着一本书坐到架下,但又常常是未看到几页就已入神,于是便随缥缈的思绪畅游,演绎、编织自己的故事。那里有绝对的真爱,并常常被“蒹葭苍苍,白露留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所打动。
这个入境太深太切的世外人,便开始回绝和排斥这个充满机心、充满是非的现实世界。我独自往来于家和学校,常常是不走大街而走小巷,而且是踏着铃声进教室,放学则是第一个冲出校门。孤高的我让人难以接近又充满好奇,像一个谜让人费解,像一本书极具个性。不愿把自己沉浸于周遭事物,不愿进入生活的角色——我喜欢清纯和随意。
[NextPage]
四
记得我几岁的时候,已是一个充满侠气和野性十足的小孩。那时,望子成龙的父亲常常因哥哥的调皮而大发脾气,于是他和母亲便在哄我入睡以后,将哥哥拉到花园进行竹杖教育。只要一听到哥哥急切的“妹妹救我”,我便会从床上跳起,全然不顾曾被哥哥欺负的狼狈而全力相救。
不知是何原因,在一年暑假,我们和街对面的小孩发生了一场“战争”。两队人马各有一二十人,大的有十几岁,小的如同我的年龄四五岁,当时十三四岁的哥哥是我们的司令,我们作好安排,拿出各自家里用牛尾或马尾作的蚊帚,让前面大一点的孩子顶在头上装扮成几个“厉鬼”,后面小一点的孩子则拿着扫帚作“小鬼”样,这样精心布置下来,认为绝对可以吓得“敌人”魂飞魄散。
傍晚时分,我们按约定时间集合,遗憾的是由于父亲要检查作业,我们的司令无法亲自指挥作战,不过这也无妨,因为我们个个斗志昂扬。等赶到约定地点,还未看清“敌人”的装束,前面的“厉鬼”们便开始张牙舞爪,后面的“小鬼”也接着起哄,我作为司令的警卫,便跳叫着鼓战。
突然一阵抽打声,“厉鬼”们已开始抱头鼠窜,接着有的“小鬼”号啕大哭起来。原来,普遍年龄比我们大的敌方拿着的是充当武器的皮带,双方相接便挥鞭抽打,看看我方绝对吃亏,顾不得掉进小河的拖鞋,赤脚便往家跑。“快开门,快开门,我们打输了。哥,快出来救人啊。” “你先回来,哥哥马上就出去。”只听得母亲一边开门一边大声说着,我闪进门,急促地喊:“哥,快出来,快去救人。”不见哥哥回音,只听得门被母亲拴上了,“你哥在里屋做作业,你也别想再跑了。”我气急败坏,跑进里屋,只见父亲正手执教鞭守在哥哥身边,看着愣在那里的哥哥,我不觉“哇”的一声哭了。
[NextPage]
五
不知是岁月载不动我的老沉,还是我拖不走岁月的积淀,很早便将自己定格在了离群索居一类。年轻飞扬的脸上写满着青春与锐气,但老早就将人生的主旋律定为“悲伤与愁苦”。记得我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当知了发出第一声呜叫
我才惊奇地发现
日子不经意地从生命之树上一叶一叶地飘落
凝聚了岁月的树身就越来越单薄了
我不敢说我还拥有很多
也不愿满怀深深的自信离去
又再拖着写满倦意的脚步伴着空虚归来
我喜欢静静地体会狂欢后的恬谧
喜欢月色下半梦半醒的宁静
喜欢在诗词字句里迷失自己
喜欢默默地斟饮那杯清淡如水的孤寂
还喜欢痴痴地感受那腔如诗如画的情怀
我又何尝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在距离
我也没有刻意地去武装自己
我也不是一个天生孤独的人
只是
在孤清和热闹中
我更钟爱那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寂寞
因为在这个时候
才可以在那完全属于自己的王国里
无拘无束地想自己的问题
细细地用心灵去咀嚼那一尘不染的青涩
我想
这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附丽
我不会忘记童年朝看东流水
暮看日西坠的争吵笑闹日子
那一切好幼稚好单纯
我珍惜那留在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
但如果再重复一次
我会受不了那抹无知的苍白
我不懂太多的世事
只愿这一生无怨无悔
走出自己的风骨
我不知他日刻下的脚印
是深沉还是浮浅
是凌乱还是清新
我只能在那份执著上抹上几笔行云流水的飘逸
只能为那层朦胧的诗意和上淡淡的韵律
尽量使自己在潇洒中不失稳重
在深沉上不失精彩
不管迎接我的是粘衣的冷月清风
还是遍体伤痕
我不会放弃那份执著的追求
至少
追求的过程是美丽的
也许让人难以想象,一个处在花季的少女,会具有这种心态。
- 上一篇: 为什么选择出家——序
- 下一篇: 为什么选择出家——寒岩枯木巅 一点早梅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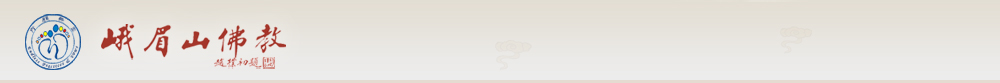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18102000121号
川公网安备 511181020001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