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及峨眉山僧侣,过去似无专文论述,本文根据史籍作一钩稽,不当之处,祈望方家赐教。
一
两晋以前的巴蜀佛教,史籍没有记载,甚至隋唐的有关载籍还明确说蜀汉时期巴蜀地区没有佛教。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说:魏、蜀、吴三国鼎峙,其蜀独无代录者何?岂非佛日丽天,而无缘者没睹,法雷震地,比屋者弗闻哉!且旧录虽注《普曜》、《首楞严》等经,而复阙于译人年世。设欲记述,罔知所依,推人失翻,故无别录。就是说,在魏、蜀、吴三国中,只有蜀国没有经录,旧的经录虽注有蜀的《普曜》、《首楞严》等经,但却没有译人和年代,如果记述它,却又没有依据,所以没有别录。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八道宣等《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说: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时军国谋猷,佛教无闻信毁。即是说,在刘备、刘禅统治蜀汉的43年中,因忙于军国大计,没有听说他们信仰佛教或毁坏佛教。但是,这仅是指刘备、刘禅等统治者而言。统治者不信仰佛教,不等于民间也不信仰。只不过统治者不信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的信仰。同样的道理,经录没有明确记载蜀汉翻译有佛经,也不等于蜀汉就没有佛经的传播。西汉末,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授《浮屠经》,就是口授的。
载籍虽没有两晋以前巴蜀地区佛教的记载,甚至还有明确否定蜀汉时期巴蜀有佛教的说法。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地区却发现了一些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的佛教考古文物。1940年在四川乐山城郊麻浩及柿子湾发现了东汉后期的崖墓。麻浩的一座崖墓的后室门额上,有一尊浮雕的坐佛像。像高37厘米,宽30厘米,结跏趺坐,头绕圆形项光,高肉髻,身上似披通肩袈裟,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即右手上举,伸五指,掌向外),左手似握衣端。在此墓附近与其风格相同的一些崖墓表上,发现有汉顺帝“永和”与汉桓帝“延熹”等年号铭文,可证其为东汉后期之崖墓。柿子湾的一崖墓中后室也发现一尊保存稍好的佛像,其造型技法与麻浩佛像大体相同,只是头上肉髻更高些,项光要小些。20世纪40年代初,还在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内发现了摇钱树陶座,其底部有双龙含璧图像,身部有三人,皆凸成浮雕状,其中间一像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两侧之像站立而侍。这是一佛二菩萨像,中者为佛,两侧为菩萨。1989年在四川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中也发现一株摇钱树,树干上铸有五尊形体相同的佛像,各像高6.5厘米,结跏趺坐,头顶有肉髻,头后有椭圆形项光,双眼微合,两耳较大,上唇有髭,穿通肩衣,右手竖掌,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左手握拳执衣下摆④。1986年四川省博物馆在什邡皂角乡马堆子发现一座东汉画像砖石墓,其中有一块残破的画像砖,厚7.5厘米、长21厘米,宽15厘米,从砖的形制和质地看,无疑是东汉画像砖。此砖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1981年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15座蜀汉墓,出土器物近3600件。其中5号墓发现一些扁长陶俑,额上眉际有类似佛教的“白毫相”。又在5号墓和14号墓中发现清理出铜树树干十四节,每节树干上均有一佛像,为双范合铸的圆雕佛像,与树干成一体,像为坐式,高5.6厘米,宽3.5厘米,头顶有高肉髻,圆眼高鼻,眉毛隆起,鼻梁修长,两眼平视,神态端庄,身着宽松长衣,结跏趺坐,右手前伸,手掌直立,五指并拢,掌心向外,似作施无畏印,左手握住下垂的襟袖一端。
上述发现的佛教文物,在时代问题上,近年又有新的判断,有说乐山麻浩佛像属于蜀汉时期,柿子湾佛像值汉、蜀之际;什邡佛塔画像砖可能晚至蜀汉;彭山摇钱树坐佛像与绵阳何家山摇钱树佛像当在建安至蜀汉时期;忠县涂井陶俑在蜀汉后期。总之,都在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是无问题的。这就说明,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有佛教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从何而来呢?有说是从南方云南方向传来的,但证据还不充分;又有说从洛阳“经关中蜀道或荆楚江道人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也是推测,没有明显的证据。从现有的研究情况看,还无法确定巴蜀早期佛教文化的影响来自何方。至于传播影响的人,可能是外来佛教僧侣或信仰佛教者,也可能是本地人到外地受了影响而带回当地者。但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推测,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应有外来僧侣,甚至还有本地人出家为僧者。《高僧传》卷一二《释僧生传》载:释僧生,姓袁,蜀郡郫(今四川郫县)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称,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诵《法华》,习禅定,常于山中诵经,有虎来蹲其前,诵竟乃去。《大唐内典录》卷一《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亦载:蜀郡沙门释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至目为三贤寺主。诵《法华》,习禅定。尝山中诵经,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此记载是沿袭《高僧传》的,但都没有说明释僧生的时代。《法苑珠林》(四部丛刊本)卷二六《敬法篇》云:“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从小出家,以苦行,致目为三贤寺主。诵《法华经》。寻常山中诵经时,至夜,每感虎来蹲前,部讫乃去。”可见此西晋之静僧生,即《高僧传》中的释僧生,二者的事迹完全相同。“静”字可能是“释”字之误,也可能“静僧生”为原名,释僧生为后取之名。因中国僧人以释为姓,始于东晋之道安。僧生既是西晋人,应是现在所知蜀中最早的第一个僧人。并由此可知:西晋时蜀中已有出家为僧者,成都也有了佛教寺庙三贤寺,佛教的《法华经》也已在蜀中流传。这些虽然都是西晋时期的事,但绝不可能突然产生于西晋,应有一个发展过程。再考《法华经》,即竺法护所译之《正法华经》,译于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则僧生在蜀中诵《法华经》当在太康七年之后,此时距蜀汉之灭亡仅二十几年,很可能蜀汉时期就有外来佛教僧侣在蜀中传播佛教,并渐渐修建寺庙,剃度僧侣,蜀中就有了本地人出家为僧者。
虽然,蜀中从汉末张陵人蜀传授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经张衡、张鲁三世,蜀中的五斗米道已相当流行。《法苑珠林》(四部丛刊本)卷六九《破邪篇》谓张陵所设天师道的二十四治,就有二十三治在蜀地。直至两晋时,赉人李氏统治巴蜀,也宗奉天师道。但天师道的流行,并不影响佛教的传播。汉代人往往并祠黄老与浮屠,!在上述四川的考古文物中,也反映了这种现象。故天师道与佛教可并行流传。
二
文献明确记载的外地来巴蜀地区的僧侣,是东晋时的释法和。
东晋哀帝兴宁中,北方名僧释道安躲避战乱,于兴宁三年(365)率领徒众南奔襄阳,行至新野对徒众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本,宜令广布。便分散徒众,令竺法汰到扬州、法和人蜀,说蜀中“山水可以修闲”。《高僧传》卷五《释法和传》亦云:释法和,荥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但法和在蜀中更具体的佛教活动却无记载。晋安帝时又有凉州禅僧释贤护人蜀,《高僧传》卷一一《释贤护传》云:释贤护,姓孙,凉州人,来止广汉阎兴寺,常习禅定为业,又善律行,纤毫无犯,以晋隆安五年卒。但贤护人蜀后的影响似乎不大。
东晋时人蜀影响最大的僧侣,是东晋名僧慧远之弟慧持。慧持“年十八出家,与兄共伏事道安法师,遍学众经,游刃三藏”。后道安率徒众奔襄阳,令慧远东下,慧持即随慧远到了庐山。在庐山僧众中慧持已很突出,《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云:“庐山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为称首。”慧持之名几乎与慧远并列。豫章太守范宁,曾请慧持讲《法华》、《毗昙》,“于是四方云聚,千里遥集”,盛况可想而知。
名士王殉曾致书范宁问:“远公持公孰愈?”范宁回书说:“诚为贤兄弟也。”王殉又回书云:“但令如兄,诚未易有,况复弟贤耶!”兖州刺史王恭也致书僧检问:“远、持兄弟至德何如?”僧检答云:“绰绰焉,信有道风矣。”就是远在关中的名僧鸠摩罗什,对慧持也很敬佩,“致书通好,结为善友”。后来慧持“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在传化,兼欲观瞩峨眉,振锡岷岫,乃以隆安三年(399年)辞远人蜀”。慧远很不愿慧持离去,苦苦相留。慧持却矢志不渝。慧远感叹说:“人生爱聚,汝乃乐离如何?”慧持也悲叹道:“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看来慧持信佛教之虔诚还超过了慧远。慧持辞别慧远行至荆州时,又受到荆州刺史殷仲堪及桓玄之礼敬与挽留。而慧持入蜀之心甚坚决,临去时致书桓玄云:本欲栖病峨眉之岫,观化流沙之表,不能负其发足之怀,便束装首路。慧持人蜀后,住于成都龙渊寺,于是“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益州刺史毛璩也非常敬重慧持。当时蜀中高僧尚有慧岩、僧恭二人,名望也相当高。而慧持至蜀后,二人及蜀中人士均“望风推服,有升持堂者,皆号登龙门”。后来谯纵攻杀毛璩,据有蜀土,自号成都王,又杀害高僧慧岩。慧持便率僧众避难至郫县中寺。谯纵之乱平息后,慧持又率僧众回成都龙渊寺,自此又大弘佛法,“讲说斋忏,老而愈笃”,直至义熙八年(412)去世于龙渊寺。慧持临终时,遗命弟子谨遵戒律说:“经言戒如平地,众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谨哉!”由此看来,慧持是经律并重者。慧持又将“东间经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间法典嘱弟子昙兰”。以后道泓、昙兰皆能遵循其师之轨迹弘扬佛法。东晋后期,外地人巴蜀地区的僧侣不断增多,本地出家为僧者当亦不少。如东晋康帝时巴西郡的范材。《高僧传》卷一O《竺法慧传》载:时有范材者,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初为沙门。由于僧侣众多,东晋后期蜀郡已设置了僧官——僧正。《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云:时有沙门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倾盖。……恭公幼有才思,为蜀郡僧正。僧官之出现,说明僧侣众多,需有专职管理。可见东晋后期蜀中佛教已发展到相当程度。
三
南朝宋初,巴蜀地区来了一些禅学高僧,把巴蜀地区的禅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人蜀的,当是长安的释昙弘。《高僧传》卷一一《释玄高传》云:昔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闻高被摈,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顾栈道之难,冒险从命。是昙弘曾在成都大传其道。但昙弘何时人蜀?所传之道究为何道?这里并不清楚。据上引《释玄高传》所载,玄高出家为僧后,就专精禅律。后又从浮驮跋陀禅师专习禅法,学成后,便隐居麦积山,从其学者百余人,皆“禀其禅道”。此时昙弘亦在麦积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同业,即指玄高与昙弘同习传禅业。而此时,正是西秦乞伏炽磐在位之时。乞伏炽磐在位时期为东晋义熙八年(412)至刘宋元嘉四年(427)。昙弘与玄高在麦积山友善后便人蜀,故可推知昙弘人蜀约在刘宋之初。再从河南王(即乞伏炽磐)想藉昙弘之高名,特遣使至蜀迎接他去西秦一事看,可知昙弘在蜀中传授禅法之名望甚高。元嘉初,又有禅僧畺良耶舍人蜀,《高僧传》卷三《畺良耶舍传》载:畺良耶舍,此云时称,西域人。……善诵《阿毗昙》,博涉律部,其余诸经多所该综,虽三藏兼明,而以禅门专业。……以元嘉之初,远冒沙河,萃于京邑。……后移憩江陵。
元嘉十九年,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按“元嘉十九年”当作“元嘉九年”,“十”字盖衍。《比丘尼传》卷四《昙晖尼传》云:元嘉九年(432)有外国禅师叠良耶舍入蜀,大弘禅观。晖年十一,启母求请禅师,欲咨禅法,母从之。后来昙晖卒于梁天监三年(504),时年八十三,正与元嘉九年昙晖十一岁相符,畺良耶舍实于元嘉九年入蜀。又从此例还可得知刘宋之初蜀中已有了本地出家的比丘尼。元嘉中,又有禅僧释法成人蜀。《高僧传》卷一一《释法成传》载:释法咸,凉州人。十六出家,学通经律,不饵五谷,唯食松脂,隐居岩穴,习禅为务。
元嘉中,东海王怀素出守巴西,闻风遣迎,会于涪城,夏坐讲律,事竟辞反,因停广汉,复弘禅法。
又有释慧览,亦在元嘉中人蜀,《高僧传》卷一一《释慧览传》云:释慧览,姓咸,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咨受禅要。……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天宫寺。宋文请下都止钟山定林寺。
还有西游诸地的释智猛,也于宋初人蜀传授禅法,并著《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流传于蜀中。《释迦方志》卷下《游履篇》载:东晋后秦姚兴弘始年,京兆沙门释智猛与同志十五人,西自凉州,鄯鄯诸国至罽宾,见五百罗汉,问显方俗,经二十年,至甲子岁,与伴一人还东,达凉入蜀(按《高僧传》卷三《释智猛传》谓元嘉十四年入蜀),宋元嘉末年卒于成都。游西有传,大有明据,题云《沙
门智猛游行外国传》,曾于蜀部见。
从上述记载及《高僧传•智猛传》尚看不出智猛传授禅法。而《高僧传》卷一一《释法期传》云:释法期,姓向,蜀郡郫(今四川郫县)人。……十四出家,从智猛咨受禅业,与灵期寺法林同共习禅。据此,可知智猛在蜀中亦传授禅法。
上述诸禅师虽也明律,大概人蜀后仅仅弘传禅法,故元嘉中蜀地僧人感到无好律师。《高僧传》卷一一《释法琳传》云:
释法琳,姓乐,晋原临邛(今四川崇州)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专好戒品,研习《十诵》。常恨蜀中无好宗师,俄而隐公至蜀,琳乃克己握锥,以日兼夜。及隐还陕西,复随从数载,诸部毗尼,洞尽心曲。后还蜀止灵建寺,益部僧尼无不宗奉。
据此,刘宋初蜀中之律学较弱,法琳之后才渐盛。《法琳传》中所说的隐公,即释僧隐,是元嘉时人蜀弘传戒律、禅法的高僧。《高僧传》卷一一《释僧隐传》云:释僧隐,姓李,秦州陇西人。家世正信。隐年八岁出家,便能长斋,至十二蔬食。及受具戒,执操弥坚。……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笈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高公化后,复西游巴蜀,专任弘通。
是僧隐之律学,又学自玄高。玄高是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魏平凉州后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又于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被杀于平城。则上谓“高公化后,复游巴蜀”之说不实。释僧隐之“复游巴蜀”传授戒律、禅法,当在太延五年(439)前后。而法琳之从僧隐学律学,当在太延五年之后,亦即刘宋元嘉十六年(439)以后。宋孝武帝时,又有释智称专精律部,《高僧传》卷一一《释智称传》云:释智称,姓裴,本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魏冀州刺吏徽之后也。……宋孝武时,迎益州仰禅师下都供养,称便束意归依,仰亦厚相将接。及仰反汶江,因扈游而上,于蜀裴寺出家,仰为之师,时年三十有六。乃专精律部,大明《十诵》。
刘宋中期外地人蜀的诸僧中,亦有禅律并传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释道汪。释道汪是长乐(今江苏境内)人,但幼年即随叔父住京都建康(今南京市)。十三岁即投庐山慧远而出家,其后“研综经律,雅善《涅盘》”。后闻凉州玄高法师禅慧深广,欲前往深造,而中途受阻,遂转人蜀郡成都。至成都后,即得蜀中道俗之敬重。征士费文渊即从受学,并为立寺于成都城之西北,名为祗洹寺。于是“化行巴蜀,誉洽朝野”。后因“梁州刺史申坦与汪有旧,坦后致故,汪将往省之,仍欲停彼”,并得益州刺史张悦的许可。费文渊得知后,即上书张悦说:道汪法师,识行清白,风霜弥峻,卓尔不群,确焉难拔。近闻梁州遣迎,承教旨许去。
阖境之论,佥曰非宜。鄙州边荒,僧尼出万,禅戒所资,一焉是赖,岂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愿鉴九俗之诚,令四辈有凭也。张悦即敦留道汪,道汪因此未去梁州。后来张悦返回京都,向宋孝武帝称述道汪德行。宋孝武帝即下令道汪为京师中兴寺主。道汪以疾固辞,因仍留成都。后来王景茂请道汪居武担寺为僧主,于是僧众更为清谨,道俗更加崇归。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道汪卒于武担寺。刘思考为其建塔于武担寺门之右。与道汪同时在蜀郡的僧侣,江阳寺的释普明、长乐寺的释道阉,也“戒德高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也为时人所重。刘宋时期,外地人蜀的高僧除上述外,还有释法瑗、邵硕、释道法等。本地出家的僧侣也还有释僧庆、释普恒等。由于僧侣增多,巴蜀地区之僧尼竟已上万,可谓盛况空前。
四
齐梁时,巴蜀地区佛教之风气有所转变,从刘宋时的重禅法、戒律而变为重义学。齐明帝时,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的释宝渊,出家后就想作讲论之主。《续高僧传》卷六《释宝渊传》云:释宝渊,姓陈,巴西阆中人也。年二十三,于成都出家,居罗天宫寺,欲学《成实论》,为弘通之主。州乡术浅,不惬凭怀。齐建武元年,下都住龙光寺,从僧曼法师,禀受五聚,经涉数载,义颇染神。……复从智藏采孺先业,自建讲筵,货财周赡,笃励辛勤,有倍恒日。……乃广写义疏。……因带帙西返,还住旧寺,标定义府,道俗怀钦。于是论筵频建,听众数百。
巴西僧人法绍,也长于义学。《高僧传》卷八《释法度传》云:时有沙门法绍,业行清苦,誉齐于度(即释法度),而学解优之。故时人号曰北山二圣。绍本巴西人,汝南周颛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与绍并为齐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遥光恭以师礼,资给四事。由于蜀中义学转胜,梁武帝初,“梁武陵王出镇庸蜀,闻彼多参义学,必须硕解弘望,方可开宣”。武陵王萧纪便准备选带硕学高僧一同前往,而部属所举荐者皆不合意,萧纪说:“忆往年法集,有伧僧韶法师者,乃堪此选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边服。”伧僧韶法师,即吴中高僧释慧韶。《续高僧传》卷六《释慧韶传》云:释慧韶,姓陈氏,本颍川太丘之后,避乱居于丹阳之田里焉。……十二厌世出家,具戒便游京扬,听庄严曼公讲《释成论》,才得两遍,记注略尽。……乃试听开善藏法师讲,遂觉理与言玄,便尽心钻仰。……寻尔藏公迁化,有龙光寺绰公继踵传业,便回听焉。
既阙论本,制不许住,惟有一帔,又属严冬,便撤之用充写论,忍寒连噤,方得预听,文义兼善,独见之明,卓高众表;辩灭谛为本有,用粗细而折心。时以为穿凿有神思也。
这样一位独见卓高、神思善辩之高僧,无怪萧纪要选之带人蜀中,慧韶至蜀后,果然“于诸寺讲论,开导如川流”。当时成都讲经之风气甚盛。“法席恒并置三四,法鼓齐振,竞敞玄门。而韶听徒济济,莫斯为盛”。慧韶还率“听侣讽诵《涅盘》大晶,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数集,轮次诵之”。武陵王萧纪也虔心佛学,人蜀之后,“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论,沙门宝彖、保该、智空等并后进峰岫,参预撰集,勒卷既成,王赐钱十万,即于龙渊寺分赡学徒”。后来慧韶一直居于蜀中,直至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卒于成都龙渊寺摩诃堂中。
萧梁后期,巴蜀地区之佛教僧侣除重义学外,还重文辞玄理。其中,以巴蜀高僧释宝海与释方智最为突出。《续高僧传》卷九《释宝海传》云:
释宝海,姓龚,巴西阆中人,少出家,有远志,承扬都佛法崇盛,便决誓下峡。既至金陵,依云法师听习《成实》。宝海思想敏锐,善于言辞。当时梁武帝崇重佛法,自讲《涅盘经》,并命宝海论佛性义。(宝海)便升论榻,虽往返言晤,而执钥铭香炉。帝曰:“法师虽断悭贪,香炉非钥不执。”海应声曰:“陛下位居宸极,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悦,众咸惊叹。
后来宝海返还蜀都,住于成都谢镇寺,遂“大弘讲肆”武陵王萧纪人蜀后,对宝海非常敬爱,常至谢镇寺与宝海共宿。某次,二人言谈通夜,“至旦,王将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辉粉壁,状似城中;风动刹铃,方知寺里。”其晨车盖迎王,马复嘶鸣,海曰:“遥看盖动,喜遇陈思;忽听马鸣,庆逢龙树。”宝海之善言辞皆如此。后来巴蜀人西魏、北周,宝海仍受镇将之敬重。
释智方与宝海同时,《续高僧传》卷九《释智方传》云:释智方,蜀川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童稚出家,止州廓龙渊寺轮法师所。早与宝海周旋,同往扬都云法师讲下。智方更善言辞,本传谓其“机辩爽利,播名扬越。每讲商略,词义清雅泉飞,故使士俗执纸抄撮者常数百人。”智方曾在京都讲《法华经》,讲至《宝塔品》高妙时,便说:何必昔佛国土有此高妙,即扬都福地亦甚庄严。至如弥天七级共日月争光,同泰九层与烟霞竞色;方井则倒垂荷叶,圆桷则侧布莲花;似安住之居南,类尼怯之镇北。耳闻目见,庶可联街。当时有录得此语者,带回巴蜀后,时人“叹为惊绝”,谓其“语出成章,状如宿构”。宝海对智方的言辞也很佩服,常有意激发其辞。宝海曾调嘲智方说:“三隅木斗何谓智方?”智方即答:“瓦砾污池哪称宝海?”后来智方也回到蜀中弘扬佛法,至九十余岁才卒于蜀中。与智方、宝海大体同时的还有蜀僧释宝彖,也在巴蜀地区广为传播佛经与疏解佛经。《续高僧传》卷八《释宝彖传》云:释宝彖,姓赵氏,本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后居绵州昌隆之苏溪焉。……年二十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听律典,首尾数年,略通持犯。回听《成实》,传授忘倦,不吝私记,须便辄给。研心所指,科科别致。后又在成都听慧韶法师讲经之深理奥义。当时武陵王萧纪却于龙渊寺摩诃堂令宝彖讲《观音经》。宝彖“初未缀心,本无文疏,始役情思,抽帖句理,词义洞合,听者盈席”。宝彖又将讲说录为疏本,遂广传于世。后来宝彖回到绵州,“开化道俗,外典佛经相续训导,引邪归正,十室而九”。宝彖志在弘传佛法,故“虽道张井络,风播岷峨,而志意颓然,唯在通于正法”。他见《大集经》未在蜀中流传,便“欲为之疏记,使后学有归。乃付著经律,就山修缵”。历时两年,方成传世。宝彖后来还为《涅盘》、《法华》等经作疏。“皆省繁易解,听无遗闷”。宝彖疏解之佛经,后在剑南广为流传。
在齐梁之世,蜀中还有高僧释昙凭善于转读。《高僧传》卷一三《释昙凭传》云:释昙凭,姓杨,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少游京师,学转读,止于白马寺,音调甚工。昙凭以后又不断研习,终于出类拔萃,名震当时。后还蜀中住龙渊寺。“巴汉怀音者皆崇其声范。每梵音一吐,辄鸟马悲鸣,行途住足”。昙凭还制造了铜钟,据说“庸蜀有铜钟始于此也”。
五
萧梁后期,巴蜀佛教僧侣众多,大德辈出。当西魏袭取巴蜀与荆州后,由于统治者崇信佛教,即将大批巴蜀高僧迎人长安,使南北佛教得以沟通。《续高僧传》卷一六《释僧实传》云:(周)太祖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西魏、北周派往巴蜀地区的统治者,也尊崇佛教,敬重僧侣。如《续高僧传》卷七《释亡名传》云:周氏跨有井络,少保蜀国公宇文俊重之,性爱贤才,重其德素,礼供殊伦,声闻台省。释亡名本是荆州南郡人,为本地望族。早年在梁元帝萧绎府中任职。西魏占领荆州后,亡名即人蜀中出家为僧。
初投兑禅师,兑亦定慧澄明,声流关邺。名乃三业依凭,四仪恭仰,雕纯假于禅诵,兴虑著于篇什。故宇文俊人蜀后,对亡名相当敬重。周明帝武成初年齐王宪人蜀后,亦敬重亡名。后齐王宪任满返长安,又带亡名入朝,“帝劳遗既深,处为夏州三藏(僧官)”。而朝廷又以亡名文翰可观,有经国之量,将征调入朝任职。亡名固辞不应,终生为僧。亡名著有《至道论》、《遣执论》、《修空论》、《去是非论》、《影喻论》、《淳德论》、《不杀论》等,皆为传教劝善之作。又“有集十卷,盛重于世”。周武帝天和中,谯王宇文俭为益州总管镇蜀时,还带了天竺高僧阁那崛多人蜀,崛多还翻译了佛经。《续高僧传》卷二《阁那崛多传》云:阂那崛多,……犍陀罗国人也。……以周明帝武成初届长安,止草堂寺。会谯王宇文俭镇蜀(按《周书•谯王俭传》,俭镇蜀在天和中),复请同行。于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龙渊寺。又翻《观音偈佛语经》。北周中期,在蜀中大量传经的有慧远。《续高僧传》卷二八《释慧恭传》云:释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周未废法之时,与同寺慧远结契勤学。远直诣长安听采,恭长住荆扬访道。远于京师听得《阿毗昙论》、《迦延》、《拘舍》、《地持》、《成实》、《毗婆沙》、《摄大乘》,并皆精熟,还益州讲授,卓尔绝群,道俗钦重,粥施盈积。
大概西魏初年已将巴蜀地区之大德高僧多集中于长安,留者无几。故慧远需至长安学经。慧远学成后又回益州大量传播。当时至长安学法的还有僧渊与毅法师。《续高僧传》卷一八《释僧渊传》云:释僧渊,姓李,广汉(今四川三台)人。家本巨富,为巴蜀所称。……午十八,身长七尺,其父异之,命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兴寺,……与同寺毅法师交游,二人即蜀郡僧中英杰也。相随入京,博采新异。有陟岵寺沙门僧实者,禅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学定,豁尔知津。……渊研精定道,毅博经术。……周氏废教,便还大寺。
北周中,巴蜀高僧还有专诵经者,上引之释慧恭即其中之一。慧恭与慧远相别后,慧恭即往荆扬求道。但在三十余年后,慧恭归还巴蜀与慧远相遇。
二人相遇欣欢,共叙离别三十余年。……远曰:“大无所解,可不诵一部经乎?”恭答曰:“唯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远厉色曰:“《观世音经》小儿童子皆能诵之,何烦大汝许人也!……岂复三十余年唯诵一卷经如指许大,是非阁钝懒惰所为?请与断交,愿法师早去,无增远烦恼也。”恭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遵敬者得无量福,轻慢者得无量罪,仰愿暂息嗔心,当为法师诵一遍,即与长别。”据说慧恭即于庭前结坛,顶礼升高座诵经。
恭始发声唱经题,异香氛氲遍满屋宇;及入文,天上作乐,雨四种花,乐则寥亮振空,花则雾霏落地。慧远乃深深佩服,请慧恭教诲。又如释道积,在周、隋之世唯诵《涅盘经》。《续高僧传》卷二九《释道积传》载:释道积,蜀人,住益州福成寺。诵通《涅盘经》,生常恒业,凡有宣述,必洗涤身秽,净衣法座,然后开之。再如释宝琼,也在周、隋之世唯诵《大品》。《续高僧传》卷二九《释宝琼传》载:释宝琼,马氏,益州绵竹(今四川德阳北)人。小年出家,清贞俭素,读诵《大品》,两日一遍,为常途业。历游邑落,无他方术,但劝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寿寺,率励坊郭,邑义为先。每结一邑,必三十人,合诵《大品》,人别一卷,月盈斋集,各依次诵。如此义邑,乃盈千计。四远闻者,皆来造款。琼乘机授化,望风靡服。如此广泛传诵佛经,在巴蜀僧侣中是少见的。
六
魏晋南北朝以前,峨眉山是否有佛教僧侣,史籍没有记载,传说又多不可靠,清人蒋虎臣据明人胡菊潭的《译峨籁》续成的《峨眉山志》即载有如下传说:汉永平癸女六月一日,有蒲公者采药于云窝,见一鹿足迹如莲花,异之,追至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雾腾涌,联络交辉,咸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希有,非天上耶!”径投西来千岁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末法中守护如来相教,现相于此,化利一功众生,汝可诣腾、法二师究之”。甲子,洛阳参谒二大师,俱告所见。师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见普贤,真善知识。昔我世尊在法华会上,以四法付之: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植众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救一切众生之心。菩萨依本愿而现像于峨眉山也。”蒲归,乃建普光殿安愿王像。菩萨示现始于此。
这段传说显然不可靠。永平(58—75年)为东汉明帝年号,当时虽已有佛教传人中国,但仅限于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楚王刘英之崇尚“浮屠”就是一例。关于千岁和尚(又称宝掌和尚),清嘉庆十八年刻的《峨眉县志》据《诸经发明指月录》谓千岁和尚: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生,至唐高宗显庆二年卒,住世一千七十二年,故世称为千岁和尚也。曰宝掌者,以生时左掌握,故名。魏晋间来中国,入蜀,礼普贤,住峨山灵岩寺。仅从这一记述,就可证明上述《峨眉山志》之传说不可靠,既然中印度的千岁和尚在魏晋间才来中国,汉永平中蒲公怎么可能询问千岁和尚呢?而且千岁和尚本人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千岁和尚在魏晋间已来中国,至唐高宗显庆二年(657)才去世,中间已经历四百年左右,这有无可能?加之来中国如此之久的印度僧人,在《僧传》中却又毫无记载。又上述提及的腾、法二师,是指摄摩腾与竺法兰。二人虽在《高僧传》中有传,但中国佛教史的代表作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已加以否认。认为摄摩腾之名字在刘宋以前不见记载,说他是汉明帝时人,是没有根据的;至于竺法兰,则明显是伪造的。如此说来,上述《峨眉山志》所载的有关传说,全不可靠。故周叔迦《法苑谈丛》云:相传古时有蒲翁入山采药,得见普贤瑞相,其实是宋人的附会。原因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嘉州屡奏普贤显相,因遣内侍张重进前往庄严瑞相。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0),又造普贤铜像,高二丈余,建大阁安置。其后屡加装饰,增修寺宇。于是峨眉山成为普贤菩萨的圣地。普贤在峨眉山显灵之说虽是宋人的附会,但峨眉山在宋代以前的确已成为佛教名山之一。两晋时,佛教僧侣已向往峨眉山。前面论述的东晋哀帝兴宁年间,北方名僧释道安为躲避战乱率领徒众南奔中,曾分散徒众,令法和人蜀,说蜀中“山水可以修闲”③,当包括峨眉山在内。其后慧持人蜀,目的之一就是“欲观瞩峨眉,振锡岷岫”;慧持在与桓玄书中也说:“本欲栖病峨眉之岫,观化流沙之表。”不过,法和与慧持在峨眉山的事迹史籍没有记载。而传说慧持到了峨眉山,还修建了峨眉山的第一座佛寺——普贤寺(即今万年寺前身)。但从《高僧传•释慧持传》看,慧持人蜀后,住于成都龙渊寺,大弘佛法,还得到益州刺史毛璩的敬重。后因谯纵乱蜀,攻杀毛璩,据有蜀土,自号成都王,又杀害佛教僧侣。于是慧持率僧众避难到了郫县中寺。至谯纵之乱平息后,慧持又率僧众回到成都龙渊寺,最后还在龙渊寺圆寂去世。《高僧传》却只字未提及慧持在峨眉山之事。如果慧持真在峨眉山修建了第一座佛寺普贤寺,这是何等大事!是不会不言及的。又传说峨眉山顶有老僧树,是慧持人定处。《峨眉山志》卷四《高僧》“慧持”后《附考》亦谓,“按《高僧传》载持卒于龙渊”,“未知孰是”。可能慧持到过峨眉山,仅观瞩而已,并未有佛事活动,故史籍未载。南朝萧梁时蜀僧宝彖大概也曾人峨眉山传经,《续高僧传》卷八《释宝彖传》谓宝彖“道张井络,风播岷峨”。但其详情仍无记载。此外,《峨眉山志》还说晋时有西域僧阿罗婆多尊者“来礼峨眉,观山水环合,同于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场。山高无瓦埴,又雨雪寒严,多遭冻裂,故以木皮盖殿,因呼木皮殿”。《峨眉山志》还据《杂集》记叙了明果大师,谓明果大师是资州(今四川资阳市)人,幼年出家,曾在大兴善寺见西晋僧人竺法护,回蜀后即居峨眉山宝掌峰。当时峨眉山中还有道教庙观,其中在中峰的名乾明观。观中道士每年三月三日皆作升仙之法,明果大师知是妖孽作怪,便埋伏猎人俟候,果然射中一白蟒,寻至蟒穴,见不少冠簪白骨。道士方悔悟,遂拜大师为师,并将乾明观改为中峰寺。上述这些记载未见其他载籍,未知确否。
《峨眉山志》卷三《寺观》还谓黑水寺“创自魏晋肇公”。未知此肇公是否指从鸠摩罗什译经的僧肇。据《高僧传》卷六《释僧肇传》,僧肇乃京兆(治所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出家后未离关中,及鸠摩罗什至姑臧(今甘肃武威市),肇僧始赴陇西。后又随鸠摩罗什返回长安,遂在长安随罗什译经及著述,未曾赴外地,直至东晋义熙十年(414)卒于长安,年仅31岁。是僧肇未至峨眉山建黑水寺。或肇公非指僧肇。
峨眉山的佛教僧侣,唐代以后才有较详的记载。峨眉山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也在唐代以后。
- 上一篇: 峨眉山“天下名山”的由来
- 下一篇: 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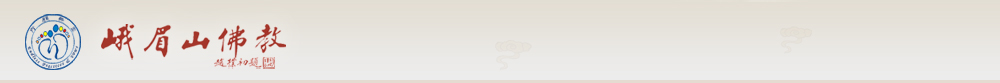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18102000121号
川公网安备 51118102000121号